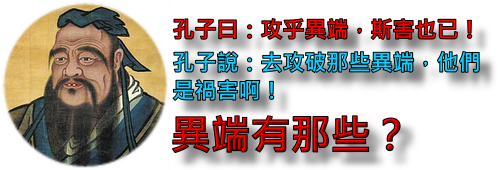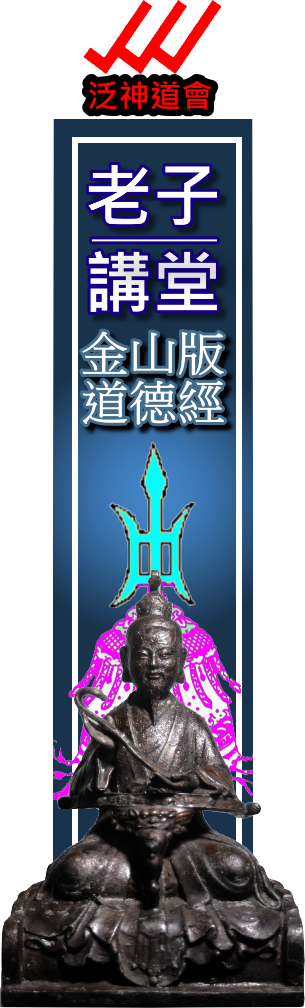孔子講學,雖然不以「天、天命、天道」 為主軸來發揮,而讓弟子有「罕言」與「不可得而聞」之嘆!但是孔子和孟子所論及的「天、天道」 ,都是有生命的,是能生成萬物,是能畜養萬物的,不是那無命不生養萬物、無體不含容萬物的「理」。
所以孔孟二儒,所講的「天、天道」 ,絕對不是宋明新儒家無命無體的「理」;所以說宋明新儒家的理學以「理」來等同「道、天道」,根本就不是繼承孔孟道統的真儒家。
宋明新儒家的「理學」強調「理」, 又不斷強調「道即是理」;其實中國更早提出「理」而有成的,是「法家」的韓非,並不是宋明新儒家。如果以「理」為主體來看,宋明新儒家「理學」的「道即是理」,是把法家韓非講的「理」,無限拉高到與「道」同等的層次;但 如果以「道」為主體來看,宋明新儒「理學」的「道即是理」,則是把法家韓非講的「道」,貶低到與「理」同等的層次。
韓非說:「道者,萬物之所然;理者,成物之文也。」原本在韓非那裡,「道」是所有定型物的形成者,而「理」是定型物的原則。所以「道」統攝著「理」,因此「道」先於「理」。
韓非的「道」和「理」雖不等同於老子的「道」和「德」,但兩者的先後關係和老子的「道」和「德」是一樣的。在韓非看來「理」不過是定型物的原則,它完全不等同於「道」。
韓非講:「理之為物之制,萬物各異理。萬物各異理,而道盡稽萬物之理,故不得不化。」就是說:「理是定型物的內控原則,所有定型物都有各自不變的內控原則,但是道卻要去完全統攝所有萬物的內控法則,所以道不得不變化。」所以說,韓非的「理」是定型物內的東西,而韓非的「道」則是控制一切「理」的東西,「理」完全不等同於「道」。
韓非講的「理」和我們現在講的「物理原則」有些接近。韓非認為凡是能夠「掌控」所有「物理原則」的,就稱之為「道」,所以韓非的「道」, 是以「控制」手段為本。所以「道」就成為韓非法家的「控制術」,所以法家的「道」就被稱為「道術」。
因此,法家韓非「註解老子」搞來搞去,神不知鬼不覺,就把老子生養萬物的「道」,替換成控制萬物的「控制術」。所以法家 韓非根本不是研究老子哲學的,也不是研究法律哲學的,而是研究君王「控制術」的。所以「法家」分為「法、術、勢」三派,這法家三派就是各取「法、術、勢」的一種,來控制 統制人民的學派,韓非則集其大成。所以法家這個學派,並不是研究法律對人類價值的學派,而是研究君王「控制術」的學派。
所以說法家看到的「道」,是統攝控制萬物的面相,不是生養萬物的面相。韓非主張萬物各有一「理」,「道」就是控制萬物之「理」的東西,所以法家一輩子就在研究如何用「法、術、勢」 ,來控制世界的「道術」。
法家沒有像老子那樣,看到萬物都是由道所生所養;法家也沒有看到萬物其實是得到道的骨血才生,失去道的骨血才死 ;萬物的生死,並不是道用法、術、勢去操控的結果。老子認為,「道」並不以「法」去主宰掌控萬物的生死,而是道以自己生命的能力來使萬物生養。所以說老子說的「道」,是以自身 的生命,是以自己的骨血,來供給萬物生命的母體,老子說的「道」絕不是以「術」來控制萬物的統治者。
老子這個「生命之道」的面相,就是老子道家,以及孔子孟子儒家積極所尋求的面相。在這個面相中,生命是最重要的,所以他們的哲學中 ,便充滿了生命關懷的「命」的思想。 所以老子講「復命」,孔子講「知天命」,孟子講「知命」,他們的哲學都是以人類實體價值為本,關懷人類生命的哲學。而他們的生命關懷,都是以「天、道、天道」之生養關懷為本,所以說中國的道儒兩家,原本都是 依於天道,價值在人,關懷生命的思想,絕不是新儒家的「心學、理學」思想。
所以說,孔孟真儒,都是講有體有命的「道、天道」,絕不是講宋明新儒無命無體之「理」。宋明新儒之「理」,雖 似源於法家,其哲學思維能力,卻又比法家更愚昧拙劣。韓非說:「理者,成物之文也。」「文」這一字,清楚說明「理」之一字,外無生命,內無實體,只是某一個定形物的原則而己。韓非又說「萬物各異理」, 由於萬物不同,其理各自不同,所以根本沒有統一的「理」,只有統攝「萬理」的「道」。
萬物之「理」既異,故「理」只有多元之「理」,「理」無統一之「理」。萬物之「理」既異,又只有多元之「理」,而無統一之「理」。所以「理」這個概念是複數概念,絕不是單數 概念。所以你一想到「理」,「理」呈現在你腦袋裡的,必是萬物各異的多頭形象,而不是統一的一頭形象。
就因為萬物之「理」各異,所以「理」字,其字義是複數不是單數,所以「理」是二或三或多,不是一。理既為多,所以「一理」這兩個字合在一起的概念,是矛盾的悖論。就像你說世界上有某東西是「一種很多種、一個很多個、一隻很多隻」就是悖論。
所以說宋明新儒家講的「理一、一理」或佛教講的「法一、一法」本身就是矛盾的悖論,這就像講「三等於一,一等於三」一樣,是邏輯不通的東西,所以新儒家的「理一分殊」,從「理一」開始的立論就不通,就是悖論,就應該被批判丟棄,所以其後「分殊」的問題,就根本不值得討論,即使接著討論出來的結論,也必定是錯的。
或許新儒家會認為形成狗的「理」,或狗行動的「理」和人是一樣,所以結論是人和狗的「理」也是一樣的。但是正常人所見卻不是這樣的。正常人所見必是「萬物各異理」,必是狗有狗理,人有人理。如果新儒家說「人與狗之理一也」,那願意相信的人,就不妨學著狗在地上爬的「理」,當一隻狗好了。
所以說,世界上根本就沒有「理一、一理」或「法一、一法」之學。我們從某方面看到不同事物的「理」,有時候確實一樣;但我們從另一方面看不同事物的「理」往往不一樣;我們不能因為只見到一樣的那一面,就說這些事物的「理」都是一樣,而作出「理一、一理」的荒唐結論。
朱熹說:「蓋以乾為父,以坤為母,有生之類,無物不然,所謂理一也。」朱熹只看到多數動物,雄的當爸爸,雌的當媽媽,就說所有生物生小孩的「理」都一樣,就作出了「理一」的結論。這個結論頂多是動物生小孩確實「理一」,但是禽獸行動有飛有爬,和人用兩腳走路就不是「理一」,你不能拿生物間片面局部的「相同」,來代表全面整體的「相同」,所以「理一」最多只是片面的真理,絕不是總真理,所以不能用來作為哲學的總真理。
如果朱熹活在現代,在顯微鏡下,知道有些生物,根本就是無性生殖,他就不會再講「蓋以乾為父,以坤為母,有生之類,無物不然,所謂理一也」這種「理一」的鬼話了。
新儒家頭腦裡充滿了「理一」的悖論,所以他們看到什麼都是一樣的,「中學、西學」,「儒、釋、道、耶、回」,他們一看過去,全部都是「理一」,就全部先用「理一」套上去之後再講。
所以新儒家和新儒家的徒子徒孫們受到「理一」的制約,見到人開口閉口就是講「一」,開口閉口就是講「理一」,開口閉口就是講「法一」,開口閉口就是講「律則一」,開口閉口就是講「心一」,開口閉口就是講「性一」,開口閉口就是講「道一」,開口閉口就是講「天一」,他們無論遇到什麼不同的學問或宗教,一定會先用「理一」的悖論,將不同的學問或宗教渾在一起,讓你誤以為全世界的思想都是一樣的。
所以這些不同的「中學、西學」,「儒、釋、道、耶、回」,就全被新儒家的「理一」渾在一處了。中國很多人被新儒家這種「理一」的悖論所影響,被新儒家這種「理一」的大框框先框上去之後,日久之後,就根本沒有講「分殊」的能力,腦袋就渾成一團了。
這世界上的事物,既然不同,就是「萬物各異理」,就應該讓萬物在保持「萬物各異理」的本來證據狀態下,去研究其間的異同。你不能先把他們全部拿到果汁機裡打渾在一起,然後再回頭來研究他們的差異,如果這樣研究,就是學術方法的錯誤。
所以宋明儒家雖講「理一分殊」,但新儒家最後就只剩「三家會通」之學,而沒有出現「三家分殊」之學,就是因為他們一開始,就先把「儒釋道三家」用「理一」的果汁機打渾了,把「儒釋道三家」弄成一團糊了,如此他們再怎麼研究分殊,也不能見到三家本來的分殊面貌了,如此所研究出來的分殊也就是糊塗的假分殊,而非真分殊了。
宋明新儒家提出「理一」,當代新儒家繼承「理一」,以及新儒家的同路人不斷講「理一」,當然是有目的的,因為他們的學問既無能力繼承孔孟儒學的天道道統,也不敢承認偷學自道家老子、佛教釋迦牟尼。新儒家是假儒學、假道學、假佛學,是孟子講的「齊丐之學」,所以他們把「儒釋道三家」用「理一」搞渾了之後,他們才能在渾水中摸魚,這就是為什麼當代新儒家和他們的同路人,至今仍死抱著「理一」不放的原因。